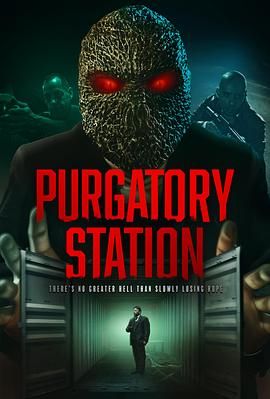Orson Welles 真會將自己身世放入角色裡頭搞出一場被害者見證大會,時不與我的天才,沒有人明白,沒有人認同的悲嗚,他自覺走前人多十年,自比高人一等,這是 Welles 的人格缺憾,他的表演方式令電影走向更個人化,作者的色彩,他也是作者論下的得益者,令他成就傳奇 Welles 的莎翁三部曲好比柏索里尼《明知故犯》(或者柏氏也是向他參考吧 ),同樣具自傳性,看者不知但處處心領神會,他們都是被命運,宿命所玩弄之人,所以Welles 要演出這時代丑角,是暗指作為電影洪流中作的推手,反被當時得令者所拋棄,是指責當時的電影圈中人 幾年後他拍《明知故犯》指涉得更明顯 嘻皮笑臉來隱於自己的慾望和不滿,自身被咀咒,只好犧牲自己來成全他人,無論作為人還是藝術家,他的故事還是由他來講的故事都太動聽 但我們可還有其他路徑來理解他的所作所為
Welles 的莎翁三部曲好比柏索里尼《明知故犯》(或者柏氏也是向他參考吧 ),同樣具自傳性,看者不知但處處心領神會,他們都是被命運,宿命所玩弄之人,所以Welles 要演出這時代丑角,是暗指作為電影洪流中作的推手,反被當時得令者所拋棄,是指責當時的電影圈中人 幾年後他拍《明知故犯》指涉得更明顯 嘻皮笑臉來隱於自己的慾望和不滿,自身被咀咒,只好犧牲自己來成全他人,無論作為人還是藝術家,他的故事還是由他來講的故事都太動聽 但我們可還有其他路徑來理解他的所作所為